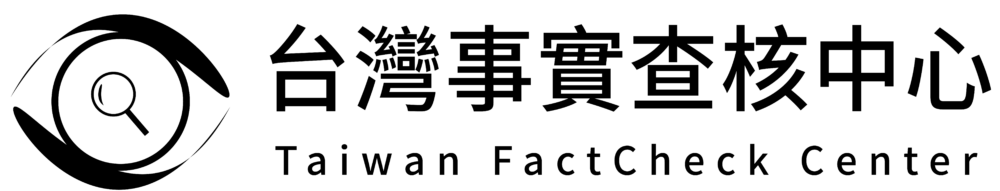?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新聞真假掰】《人選之人》引發台灣#MeToo風暴—戲劇與權勢、性、壓迫「我們不要這樣就算了!」專訪林君陽(導演)(逐字稿大公開)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新聞真假掰】節目資訊
播出時間:每周日 17:05-18:00
收聽方式: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官網 60 天隨選收聽
?邀訪來賓
林君陽 導演
?訪談精華短片
?完整訪談內容Podcast
?節目介紹
台灣第一齣政治幕僚職人劇《人選之人-造浪者》叫好又叫座,劇中一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給了許多性騷擾受害者勇氣,掀起一波 #Metoo運動,影響力驚人。
導演林君陽除了打造《人選之人》熱潮外,《茶金》、《疫起》都是他執導的作品,更以《我們與惡的距離》奪下第54屆電視金鐘獎戲劇節目導演獎。觀眾常常透過他的作品看到許多社會議題,進而讓社會有更多的思考、對話,但他卻說在執導的過程,絕不會讓「議題先行」。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成功被形容是為台灣戲劇圈注入了活水,《人選之人》帶給受害者發聲的勇氣更是社會一股重要的能量。本集節目邀請金鐘導演林君陽,聽聽夯劇背後的執導工事。請收聽「新聞真假掰 」,假訊息Bye Bye。
林君陽(導演,以下簡稱「林」)
黃兆徽(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顧問/台大新聞所兼任助理教授,以下簡稱「黃」)
?節目預告
2023/07/23 周日 17:05-18:00 全台皆可收聽(查閱各地收聽頻率)
AI孫燕姿違法嗎?「可信任的人工智慧」歐盟如何立法?五秒鐘原則的工作最容易被取代?
專訪葉奇鑫 達文西個資暨高科技法律事務所所長
?最新精彩內容
《人選之人》引發台灣#MeToo風暴—戲劇與權勢、性、壓迫「我們不要這樣就算了!」專訪林君陽(導演)
————————————————————————————————————————
林:拍的過程,我覺得太多小小的細節需要不停地做決定,尤其做為一個導演,那我覺得一種初心,就是我想要去喜歡這些角色,我想要去讓這些角色變得可愛,這個是我覺得我的初心,那我的初心不能夠變成是我想要透過這些角色把這個題目去影響社會大眾,我覺得這件事情會有很大的問題。
黃:哈囉!大家好,我是兆徽,歡迎來到新聞真假掰,今天來到現場要陪伴我們一起提升媒體素養的好朋友是導演林君陽,君陽好!
林:兆徽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黃:君陽,最近有一齣非常叫好叫座的電視影集,叫做《人選之人》,這是大慕影藝跟公共電視合製,然後Netflix(OTT服務公司)平臺率先播出,公共電視是要下半年度才會在電視上可以看到的,《人選之人》,可不可以大致跟我們介紹一下《人選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然後呢,透過《人選之人》,您想傳達什麼樣的理念?然後我們接下來想跟君陽談談,從《我們與惡的距離》、《茶金》,君陽拍過非常多很叫座叫好的影視作品,那為什麼你決定留在臺灣拍片,那面臨的挑戰又是什麼?我們來談談,那我們先從《人選之人》到底它要傳達什麼理念談起。
林:其實我有一點點辛苦的是其實很多人都會從一個所謂,你想要用作品傳達什麼理念來討論一個導演好像必然會有的所謂的有話要說。
黃:是。
林:確實有話要說啦,但是其實就是因為它很難一言以蔽之,所以我們才需要有一個這麼長篇幅的一個劇集故事去跟大家分享這些題目,那《人選之人》有點複雜,第一個事情是從源頭開始討論這件事情就是,臺灣的題材、到底什麼樣的題材是可以把它戲劇化,然後同時具有臺灣的自己的地域特色,然後同時又有機會讓國際不同的市場的觀眾看到而有所共鳴的,這個我想是在臺灣的戲劇界大家都一直都不停地在討論。
黃:追問、探索。
林:對,那早個20年,可能那時候的答案是偶像劇,討論愛情確實是一個普世價值,有機會去跨到不同的文化裡面去跟大家一起溝通,就像韓劇一開始其實也是戀愛的戲碼,然後能夠傳播出來,那其他的一些比較回到可能很韓國的自己的文化根源的東西,你可能會覺得隔靴搔癢沒有感覺,同樣的感覺其實回到臺灣,我們也一直在找所謂臺灣的自己的文化,到底有什麼東西是值得一說的,那政治、選舉就是其實我們每天都身在其中,但是很難擺脫掉,然後又覺得很有趣,但是其實又都不敢去說的一個東西,我覺得不敢去說,我覺得包含了可能從早年我小時候,很多人的小時候,我們都很習慣去從一個所謂,那時候黨國威權還蠻大壓力的一種環境裡,教育體系上來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會被提醒說那個不要講、不要討論。
黃:即使你這麼年輕,你小時候也有這樣的感覺?
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高中的時候,我參加高中的社團是那個臺灣文學研究社,然後它沒有在討論政治啦,但是它確實就是因為會去回溯、去觸碰,譬如說賴和,譬如說早年的一些臺灣文學作家,於是就會比較有本土意識的去理解臺灣的過去這幾十年的一些歷史脈絡,那就會跟課本有些不同,我讀高中大概是1997到1999,在那個狀態底下其實政黨還沒有輪替過嘛,所以於是你就會有很多的一些討論會帶著某一種年輕人的偏激,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們去臺中女中做一些交流,然而後來回到彰化的過程當中,我們在一個火車上,然後我們就幾個社團同學就一起大放厥詞的討論這個事情,就是跟歷史跟政治跟文學很多的討論這樣子,那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會蠻好笑的,但是我印象比較深刻是,下車的時候,隔壁坐著一個算是媽媽的一個女士就語重心長地跟我們說:「少年誒,這些事不要在公眾場合講,你不知道旁邊聽的是誰。」那時候就有一種覺得好像雖然已經解嚴了,雖然已經時代很不同了,但是……
黃:還是有一些人會有自己的心理審查的機制。
林:就是講到現在其實也都還是嘛,就是好像你不知道這個社會上面,你在討論的人會不會因為某一些相對有顏色,或者是有某種議題傾向的一些討論而去激怒了,或者是激發大家的討論,臺灣人我覺得有一種害怕爭執的一種天性吧!
黃:就是在實體世界裡面以和為貴,但在網路世界裡面……
林:對,那就是另外一個世界,就是大家戴上面具之後,某一種另外一方面的天性。
黃:藏在鍵盤之後就……
林:那就是另外一種,一種能量會出現,所以回到《人選之人》,其實某個程度上我自己這一端的理解會是這樣,我覺得政治值得一做,臺灣的政治文化值得一說,好的部分是我們花了30年的時間,從黨國威權一路走到現在的民主。
黃:是,臺灣的民主化。
林:那個民主化的過程其實很特別。
黃:是。而且其實是非常快速的。
林:非常快速。
黃:我們是30年,歐美是300年。
林:對,那這個快速也就造成了臺灣自己特殊的某一種情境狀態,然後臺灣人的某種民族性會讓這些東西就有很多歡樂的部分,比如說早年的……比如說中壢事件那時候最早的那個許信良,他們在做那樣子的一個選舉convene(召集)的時候,學習來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所謂的嘉年華,他們想要把選舉做成一個嘉年華這樣子,那是一個濫觴,那之後後來大家在選舉期間會聽到競選歌,然後要造勢晚會,要有很多的一些campaign(活動),其實是伴隨著歡樂的一種狀態,那當然早年可能在90年代會有多少帶著一些悲情。
黃:是。
林:但是我想在近幾年,如果你有經歷過一些政治場合的話,它好像不全然只是悲情,也不全然只是要去吶喊、訴求你的不管是痛苦也好,或者你的想要做什麼事情,可能包含了一種政治參與,其實是一種闔家歡的一種狀態,那這個就是其實《人選之人-造浪者》這一個故事跟政治捆綁在一起,我們想要去說臺灣政治的什麼呢?某一塊其實我們是這麼定義的,就是臺灣政治可不可以是一種嘉年華的狀態?參與政治不一定要帶著某種悲憤跟必須要推翻什麼的一種心情,然後來進入,政治本來就眾人之事,我們在政治場域裡面,我們可能可以討論到意識型態,我們也同時會去討論到很多家事,比如說民生議題,或者跟你我相關的某一些真的無關意識型態的一些題目,那討論這些題目的時候,可能沒有那麼的博大精深,就是你跟我有那麼那麼大的鴻溝距離,我們好像可以一起去討論這些東西,相對理性。對,那在這種狀況底下,其實參與政治就會變成一個可能會比較soft(柔軟)一點點的狀態,那在這樣的狀態裡面,我們開始講關於政治的故事,選擇的一個切點不是檯面上政治人物,而是檯面後面的那些所謂的造浪者。
黃:幕僚,是。
林:那幕僚其實也是因為做了這個故事,我才有一些接觸。對。其實我本來對政治圈其實是有點距離感的,那參與了這樣子的一個故事去接觸到真實的幕僚,田調的過程以及實際拍攝過程,必須要把某一種幕僚的樣態給拍攝出來嘛,你就會感受到說,原來臺灣有這麼多政治幕僚,它真的是可以說是一個產業,那看著其實有一些陌生的部分,但同時也就會有很多好有趣喔,好像我的身邊的朋友的感覺,因為他們在做的事情,其實跟廣告公關公司很像,他們在短時間之內聚集起來要去打一場選戰,就好像是廣告公司,或公關公司接了一個案子,我們要完成一個半年的campaign,然後要賣一個商品,然後要想方設法地把某個東西、訊息給推出去。
黃:推出去。
林:一波又一波,然後對手……競爭對手有什麼樣的訊息?我們要怎麼回?被污蔑了,我要怎麼樣去反映?這些東西我們就是透過田野調查的過程去採訪了蠻多的政治幕僚,然後我們國民黨也去了,民進黨也去了,然後就看到他們現在的所謂的文宣部,其實他們都不叫文宣部,在劇裡面我們把某幾個現實生活當中的政黨的不同的部門,把它combine(結合)在一起,形成所謂的文宣部,其實它整體在討論的事情就會囊括了可能新聞部、囊括了公關部,然後還有甚至組織部的某一些面向,比如說我們這裡面文宣部,還要去參與那個晚會。對,那現實當中,其實組織部跟其他的一些部門可能才是這個晚會的主力,但是我們就把大概大略囊括起來,然後塑造了一群小夥伴們要去打一場選戰,那我們的視角就跟著這群小夥伴,那其中有主任、副主任,然後還有組員,主要的角色其實都是在這群人裡面,然後他們各自就背負了一些各自的故事,那主任這邊就是長年、20年的一個政治工作者、競選工作者,為了所謂的社會大眾,他覺得大的事情他犧牲小我,犧牲了自己的妻兒的某一種陪伴跟一種家庭日常,然後去工作,那他覺得自己很偉大,自己覺得自己有所為而為的,所以你們應該要等等,我做的事情比較大,那他的問題當然就會來了嘛,就是到底什麼事情會大過自己的家庭呢?就是回到家競主任,黃健瑋主演的這個角色跟自己的妻子這條線,就政治幕僚的辛酸,OK,這個是一個。
黃:大我跟小我之間的拉扯。
林:對。這就是一塊,那回到翁文方,就是謝盈萱主演的這個角色,她在講的這個故事就會回到……因為她自己身份上是個同志、前議員,她落選了,所以回到黨部這邊有一個職缺,她作為一個發言人,可能未來還會再選吧,那在她身上就會有一個同志身份認同的問題,以及所謂的同志出櫃,然後在現在現實當中的政治環境裡面,雖然已經有了,而且不算少,但是其實他們有……
黃:仍然面臨很多。
林:很多問題,對,很多的不管是……也許算是歧視吧,或者他們需要去比其他人更大聲去疾呼的事情,才有辦法去得到一個相對公平的……
黃:比較平等的待遇。
林:對,或者是討論的空間。對。那這個角色其實就在這樣子的利基點上面,站在同志的基礎上面去討論,那當然她也會有跟她自己家人的一些相處的問題要發生,然後再來第三個算是主線嘛,就是張亞靜,王淨飾演的這個角色,她是一個小黨工,文宣部的小黨工,在處理這些網路小編的一些反應,那她身上揹著一個就是#MeToo的事情,其實我很難講她是#MeToo。對,應該是說……
黃:性騷擾的事件。
林:性騷擾事件,權勢性騷的一個事件,然後可是我們在這個故事裡面,其實讓它相對複雜,因為她某個程度上承認自己曾經愛上過那個……
黃:是。
林:性騷擾的對象,那你在旁邊看,你會覺得這是一個不被允許,而且不被祝福,甚至不能夠容許的一個事情,不管從哪個層面來說,但是角色本身其實是站在一個「可是當年我是真的愛上他了」,這樣子一個其實很tricky(棘手的)的一個狀態。
黃:是。
林:於是就很多事情可以討論了,旁邊的人會告訴她你別傻了,譬如說文方可能就會告訴她說不管當年你們關係到底是什麼,一段關係的結束就應該結束了,那有一些事情就不能夠拿來作為一個威脅,那這個就是又討論到了關於……數位性暴力大概也就是在她身上其中的一個題目,那所以我們討論到事情蠻多的,就是透過一個所謂的政治劇,政治職人劇,然後同時觸碰到了一些些不同層面的議題,那其實都會綁回這些身處在幕僚職務上面的角色。
黃:君陽的戲,從《我們與惡的距離》到現在的《人選之人》,其實裡面都包含了非常多的社會議題,甚至每一集其實都很刻意要融合很多社會議題在裡面讓觀眾可以思考。
林:不能講刻意啦!
黃:沒有刻意嗎?
林: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剛好這幾個題目,比如說《茶金》就沒有那麼多所謂的社會議題,畢竟它有一個時代性,我們不太容易去講70年前的什麼事情跟現在社會有關,我們拿《茶金》來討論好了,其實都會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們現在要說故事,要說70年前的故事,或者我要說一個政治幕僚的故事,然後或者我要說一個加害者、被害者家屬的故事,這些故事我們要說的對象,觀眾都是當代的觀眾,那我們不會去預設說,誰是我們的觀眾,當然可能行銷端會有很多討論,那事實上我們在討論這樣子的故事的時候,是不會特別預設說我只給什麼高端菁英份子可以有討論的社會空間這樣,或者是說我要讓什麼普羅大眾什麼的,這些討論有時候會出現,但是其實最終我們都還是回到說這故事該怎麼說,它就應該是什麼的樣態,那討論議題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會比較回到說,其實我們是想要去關心某一群人,要去關心這群人,去看到他們處境的過程當中,我們自然就會往他們的為難之處去找,那那個為難之處就會發生議題,因為一旦它從一個角色鑽進去,那它會透過媒體發聲,它就會形成一個擴大機的效果。
黃:是。
林:對。這個就是回到傳播理論裡面會發生的一個事情。對,我們講一個人的故事,但是這個人的故事對於其他人是有共鳴性的,那透過一個媒體發散出去的時候,它就會變成一個社會討論,它就被定位成一個議題,而事實上我們在討論這些東西的過程,至少我自己其實是不會把議題先行的,因為它會非常危險,非常非常危險,它會變成觀眾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會把這個去跟這個議題畫上等號,這件事情我其實覺得很危險,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做戲的人,我並不是一個社會倡議者,我也不是一個……
黃:不是一個新聞記者。
林:我也不是一個新聞記者,所以我要面對事情是我確實對於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跟這些議題有所感,但是我要小心的事情是我在拍的事情是一個虛擬的戲劇,所以我要關心的其實是角色。
黃:是一群一群的人,一個一個的人。
林:對。我要想辦法讓大家認同他們看起來好像是真的人物,然後自然到某個程度上,讓你覺得他們是可信賴的,可能真實存在的某一種角色的一個真實的人物,而他們遇到的困難,你會為他們傷心難過,然後為他們開心而開心,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戲劇裡面希望能夠做到的一個境界啦,那如果做得好,大家就會相信這些角色。
黃:是。
林:然後因為他哭,我就哭這樣子,那透過這樣子的關係,其實他們身上背負的這些題目就會被大家當成所謂的議題,而去有所討論,我覺得這些都樂觀其成,有所觀察啦,但是對於一個導演來說,常常有人說你是不是先設定說要去討論這些東西,我們才來編寫這些劇情,我覺得不完全是,當然很難說百分之百沒有。對,那尤其是這幾部片子,其實編劇其實是主筆者,那以《人選之人》來說,我們的編劇簡莉穎跟厭世姬,他們自己本身是同志,然後他們自己有參與過一些政治的現場,那所以他們在編寫這樣子故事的過程當中,確實就會融入一些他們覺得值得討論的事情,但是我覺得至少《人選》裡面,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譬如說第三集我們拿廢死這個題目。
黃:廢除死刑。
林:廢除死刑這個題目來討論,它都不是為了討論廢死而我們去把這個題目放進來,它還是為了服務角色,我們在討論,其實《人選之人》某個程度上,它其實在討論說大我小我,就是我們要為了贏而放棄掉什麼事情?或者是要為了贏而能夠接受中間的灰色地帶。
黃:妥協到什麼程度。
林:那個妥協到什麼程度,是這件事情,那廢死這個題目就會拉到這樣的討論,它其實是一個適合的觸媒,它會發生討論,它會讓一個總統參選人,你自己的形象很明確,你有你自己的主張,但是因為你要選舉,所以你必須要換句話說,不停地在換句話說,那於是我們用死刑這樣子的議題,廢死這個議題去刺激出來的是角色的轉折,那如果兼帶著你們覺得討論得不錯,那確實是因為他們有深入的田調,跟我們找了很多人的幫忙,去把這個所謂的要討論死刑,如果是一個總統候選人要被問到的時候,該怎麼樣去回答跟回應?跟可能學生該在什麼樣子的態度去跟這樣子的候選人去做應對?有很多很多的反覆的推敲,甚至包含了表演者自己,因為賴佩霞,佩霞姐她自己本身也是個學者,所以她在討論這個一個這樣子的學院的場合底下,她要去說一些什麼樣的話,對於這樣的題目的時候,她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最後大家看到那個東西是一個集眾人之力,然後想辦法讓角色因為這個題目然後有所觸發,然後讓你更理解這個角色,跟更理解這個故事想要講的事情,那同時確實我們也讓大家多理解一下廢死這個概念,它的兩方的說法是什麼。
黃:是。
林:那這個是我們……我覺得做得還不錯的一個東西。對,但是很小心的就是說,如果我們一開始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倡,提倡這個事情。
黃:某一個角度。
林:某一個面向,那我們其實就會落入另外一種……
黃:就會怕它變得很教條式的,對不對?
林:它一定就會被察覺,就是你想告訴我什麼?對,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其實在看《人選之人》的過程當中,應該不至於會覺得好像我們被教育了什麼,而是跟著這些角色的。
黃:更人性的做很多理解。
林:沒錯。
黃:是。我覺得這個也是我自己一直是二十多年是做新聞工作,也確實從君陽的戲,不管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或《人選之人》在探討的議題,雖然你說不是要故意探討議題,是要關心一群一群的人,我就發現戲劇的重要價值,就是我們在做新聞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比較旁觀的角度,然後要客觀、要公正、要查證,那我們都是一個比較冷靜的旁觀的角色,可是我們可以清楚地說議題,可是比較難讓觀眾進入這些人物的內心世界,但是戲劇你可以設身處地,因為你可以把主角的OS(內心獨白)都講得非常的清楚,他到底面臨什麼樣的抉擇?他的價值觀是什麼?他面臨哪些難處?透過戲劇真的是可以讓觀眾更能夠感同身受、設身處地,所以從《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就是在探討新聞這個行業的很多的掙扎,我們都覺得真是太棒了,就非常地傳神,然後也更能夠同感,同樣的《人選之人》也是,就是人性這個到底他面臨什麼樣的狀況?什麼樣的困難?什麼樣的糾結?還有在不公平的社會制度下,他會遇到什麼樣的為難?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我們在做新聞的時候,比較難去觸及的面向,但是透過戲劇的方式可以讓觀眾更被觸動。
林:這個我覺得是兩面刃,就是說新聞來說,我覺得新聞其實在採訪真實人物,真實的故事的過程當中,如果是在一個把故事說好的狀態底下,它其實非常有力道的,但確實它有可能會去觸及到跟拉到的人,就是我對這個題目感興趣,所以我來看這個題目,那戲劇有機會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對這個題目沒有那麼感興趣。
黃:但是因為故事很好看。
林:或者因為其他的事情,然後你被吸引到,然後你同時在意到了這個事情之後。
黃:對,你就會關注到一群,你本來可能覺得不關我的事的一群人。
林:對。
黃:他們的生活,他們面臨怎樣的不公平的制度?
林:但相對來說,寫實度就差一點點,我很難告訴觀眾說這些是真實的人物,但是新聞其實你只是隻字片語,當那是真實人物的,比如說聲音也好,或者影像也好,他真的遭遇到的災難,你其實會「哇!好真實」,真實到不忍逼視,那戲劇稍微柔軟一點點。
黃:但是因為君陽的戲,就像您說在編劇的過程,其實你們都經過長期而且很大量的田野調查,所以我覺得劇本其實都非常好,非常合理,那有一個好的劇本、合理的劇本,其實非常重要,因為觀眾才不會看到哪裡就覺得有點尷尬這樣。
林:這很重要,這非常重要。
黃:他是可以完全融入,可以完全理解。
林:劇本是最難的,劇本一直都是最難的。對。像最近好萊塢正在罷工,編劇正在罷工,那因為接下來的AI時代的很多的劇集產生的一些勞資的問題,那麼他們正在罷工,那臺灣其實沒有所謂的編劇工會,所以也不會出現這樣所謂的罷工,但是我覺得近幾年應該大家越來越清楚知道編劇的重要性,跟一個文本故事的紮實度,會如何去影響一個故事最後有機會被看到的時候的那個完整的樣態。
黃:是,剛剛提到我們透過這個《人選之人》裡面的角色,其實也談到了包括廢除死刑,包括同志,包括#MeToo,裡面其實有新移民、寵物、海洋污染的問題,#MeToo的這個性騷擾,或者說數位性暴力的問題,其實最近在臺灣,不管是藝文界、政治圈、媒體圈其實也激起了一些漣漪,很多人會覺得跟《人選之人》很有關係,甚至有些人會明白說是看了《人選之人》之後給了他勇氣,要把他被性騷擾的過程揭發出來,以免有下一個受害者,你自己怎麼看?《人選之人》對於很勇敢的#MeToo運動,你自己怎麼看?
林:本人是個生理男啦。對,所以確實在成長過程當中,比較難以觸碰到這樣子的題目,即使可能耳聞,或者是說好像經歷過某一些,好像他好像怎麼樣怎麼樣的一些事情,但是其實對我來說都還是有點難有切深的感受。對,我自己感受是《人選之人》在拍攝的過程當中,其實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故事本身確實是在討論這樣子的性騷擾、權勢性侵啊這些東西的一些討論,那這些討論我們在前期就有跟一些田調的對象聊,聊的過程我們沒有特別去聊到誰,我們確實沒有任何一個所謂的指涉說「我們就是在說那個人」的一個田調的明確的目標,但是那個過程當中,很明確的一個感受是大概是政治幕僚們都會很明顯地告訴你說,政治圈在性的處理上面是有它自己的一套邏輯的。
黃:嗯哼。
林:對,我講得很含蓄。
黃:對,一套特殊的邏輯是什麽?
林:就是因為包含……其實我覺得《紙牌屋》,我們拿一個比較遙遠的例子來講,《紙牌屋》就是一個還蠻好的例子,就是它把權跟性這件事情做了一個在戲劇上面強烈的對比,而且直接呈現給你看,在故事裡面的那一對副總統夫妻跟後來變成總統的夫妻,Kevin Spacey(凱文·史貝西)他們的演繹,中間的對於性的描述,其實有跟權力相關的一些描寫,那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單刀直入、血淋淋的、赤裸的去描述關於政治裡面的一些性的一些暗喻、隱喻、明喻,那《人選》沒有要再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們沒有在討論到那一塊,沒有用這件事情在做明喻、隱喻,但是我們在田調過程確實會有感受到很多人就是說,很多議員,或者是立委,他們有所謂工作上面長期合作的夥伴,那可能是異性,或者同性,但是某個程度上,比如說到處跑行程這件事情,你可能一年跟夥伴相處的時間,還比你的家人還長。
黃:比家人還長。
林:這就像你的第二個家,而在這第二個家裡面發生任何的曖昧,或者是你甚至可以說那是真愛也說不定,它就很容易去模糊那種道德上面的。
黃:那條線。
林:那條線,那這是一個我們在田調過程當中有切身感受到,OK,OK,政治圈確實對這件事情有某一種集體的感受,那我們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或者是我在拍這個東西的時候,我自己是沒有被綁住的,那我就覺得OK,大家都這麼覺得,那我們來用政治圈來討論關於就是性騷擾這件事情,它就會變成一個理所當然的一個舞台,那還蠻適切,我們就把故事拍出來了。
黃:所以在田調的過程中說,政治圈對於性有一些比較獨特的邏輯思想,但是你情我願是一回事,但是利用權勢性騷擾,甚至性侵害,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對不對?那也是在這個劇集裡面的權勢性騷擾,甚至數位性暴力的問題會被凸顯出來,然後也帶動臺灣這一波#MeToo的……
林:對,但我自己是很訝異的,其實就是雖然理智上知道這些事情在外面是存在的,但是當你真的看到說有這麼多的人,去很勇敢的把自己的經驗說出來,原來這不是只有政治圈的事情。
黃:從政治圈開始爆發之後,在媒體圈、文化圈其實都去引起……
林:各式各樣,對,對,對。
黃:會鼓勵到更多的受害者,他願意把他的經歷講出來。
林:對。我覺得某個程度上,這絕對是好事,然後前幾天也看到一些人的評論,就是因為臺灣在#MeToo的浪潮其實算是走在很後面的,前幾年從歐美開始,然後整個好萊塢燒了一大圈嘛,然後一直到可能韓國、日本都有相對應、相關的討論,很多的issue(議題)在那邊,那臺灣其實晚了幾年,所以其實好處、壞處都有,壞處當然就是晚了,其實有些事情……你其實有機會可能更早一點發聲。
黃:更早,避免受害者。
林:對。那好處就是說人家都走完一遍,所以其實這些東西在延燒的過程當中,可能會做的比如說過度的影射,或者是其實利用這樣子的事情去做過多過多的一些討論,那這些東西都會有一個前車之鑑可以去討論,也許我們可以快一點點地把這個#MeToo的議題,從一個有點危險的狀態去讓它往更好的方向走,就是討論該討論的,而中間有一些可能會過度延燒到不必要的一個程度去,或者其實有人藉著這樣子的題目在做任何不管是政治上面,或者是其他的一種討論,我們有機會有前車之鑑,然後去避免這樣的事情,或者有更好的討論空間,這是我覺得可能是好處的部分。
黃:是,在#MeToo事件裡面,當然我們都是很支持說,如果遭遇到權勢性騷擾這樣子的受害經驗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經驗說出來。
林:是。
黃:因為是要避免下一個受害者,也讓這個利用權勢性騷擾的人自己知所警惕,不管他最後有沒有定罪?因為性騷其實真的也不容易找到證據來定罪。
林:對,對。這是這個題目最困難的地方。對,影視裡面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選之人》裡面有提到,你被摸了。
黃:你怎麼證明?
林:你要證明,對,你要跟長官證明這件事情,那你如果無法證明的話,長官就算相信你,可能他也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來伸張你的正義,即使你的主觀是不舒服的,那這件事情你要繞回來說,那蒐證還要受害者自己來。
黃:自己舉證。
林:這件事情就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事情。
黃:對,是。但是因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可能也有一些被指控的人,他覺得他是被冤枉了,甚至有人是不是挟怨報復?面對這種狀況。
林:這就說不清楚啊,對啊,你可能真的做了錯事,或者你真的是不小心的,但是人家是不舒服的。
黃:對,其實性騷擾就是在於只要被騷擾的人覺得不舒服,你就成立了。
林:對,那這個成立就不知道,可大可小嘛,就是現在有一點點零和啦,就是有,就是完全不可以這樣子。對。那我不知道這些理性的討論空間,還存不存在?
黃:好,其實你在這齣《人選之人》裡面對於權勢性騷擾,其實也做了很多討論,包括它其實曾經是有一段愛情,那個灰色地帶會更凸顯,這個我們待會來討論,幫我們先點一首歌。
林:我會選擇《人選之人》的那首競選曲,那裡面有兩首競選歌,第一首歌是那個〈昂聲〉,就是我們特別做了一首20年前風味的一個競選歌,那另外一首是〈未來是〉,你看歌名叫未來。
黃:〈未來是〉。
林:這首歌在這個故事裡面,它有一個很特殊的位置,它是公正黨,劇中的政黨的現任在選總統大選的競選歌,而這裡面我們做了很多的討論,在歌詞上面它就是一個呈現我們想要往未來去的一個願景,那也符合我們這個故事想要說的事情,那裡面包含了一個事情是比如說語言是運用,我們在這裡面試著做了更多族群融合的事情,裡面有客語、有臺語、有……我記得應該有英文,就是基本上都用上了,某個程度上其實就是想要點出,我們現在當下臺灣的某一種共同價值。
黃:它其實是很多元的,我們先來聽聽這首〈未來是〉。
黃:我們剛剛在談的是《人選之人》,這個《人選之人》裡面在討論權勢性騷擾,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對不對?在這裡面的故事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林:其實這裡面算是跟性騷有相關的題目有兩個,裡面有都發生在張亞靜身上,那trigger(觸發)開始的時候,她是在辦公室裡面被一個算是「豬哥」(好色的人),一個同事,很愛上下其手的一個同事,愛偷摸豆腐的一個同事,然後被摸了,摸了之後呢,因為亞靜自己身負武學,她自己有鍛鍊過,所以她用了她自己的方式去把他打了一頓,那可是這件事情就鬧大了,就是主管,我們發現了之後,就是想要幫她伸張正義,我們要做性平會,但是發生了一個事情,我們整個故事就是在打一個大選嘛,總統大選的當下,然後這個政黨發生了性平事件。
黃:是。
林:很容易被對手做文章啊,於是以大局為重,這件事情……
黃:對,要不要以大局為重?
林:就被壓下來了,那當然它就會成為一個戲劇上面滿重要的一個兩難,就是你到底要站在哪一邊?兩邊都對,某個程度上兩邊都對,那其中一個事件,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大的事情就跟可能爆雷有相關,這個就防雷線,如果你還沒看,然後會希望說看完之後再來討論的話,就先關掉,另外一條線就是張亞靜這個角色,其實在早幾年的時間,她其實跟另外一個政黨的一個蠻高層的一個人,她其實有過一段婚外情,那這段婚外情,在當年因為她是一個老師學生的身份,甚至是一個上屬下屬的身份,所以它變成一種……
黃:有一種特別權力關係。
林:權力關係。對。那這個權力關係會讓某一些,也許你們真的有感情吧,但是它是在一個不對稱的一種權力關係底下發生的一個感情跟性的一些事件,這個事件就會變成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事情,那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覺得編劇很厲害,就是他們用了兩個不一樣的跟性騷有關的……
黃:狀況。
林:狀況。
黃:不太一樣的。
林:一輕一重,然後一個相對影響事件相對小一點點,就是比較單獨個人,那另外一個就是回到以大局為重的這樣的討論,那其實每一個都會回到以大局為重的討論。
黃:對,就是跟他們的職業有關係。
林:對。很重要的一句臺詞就是裡面的文方講那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
黃:我們不能就這樣算了。
林:對。所以一邊講就一邊在說就是人會慢慢地死掉。對。我們不能就這樣算了,不然人會慢慢的死掉,其實我第一次看劇本的時候,對於那一句臺詞是覺得力道非常非常強的,光是看文字就會一直……
黃:是,我們不能就這樣算了,不然人會慢慢死掉,這個死掉的意思?
林:其實我覺得當時我看到的時候,第一次的很明確的感覺是他講的不只是這個角色。
黃:性騷擾。
林:對。就是我們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fighting for(為之奮鬥)的,那我們各種原因,所以我們會覺得暫且放下吧!
黃:就算了吧這樣,對不對?
林:就算了吧!也許是正義感,也許是你應該去爭取什麼。
黃:一些理想、一些雄心壯志。
林:那這些東西慢慢的一切都算了算了算了,到最後就真的是人就慢慢地死掉了,對。
黃:就枯萎了。是。所以我們不能就這樣算了,就鼓勵了很多這個被性騷擾的受害者願意站出來,但是性騷擾當然有它的一些困難的地方,困難認定的地方,在這齣戲裡面也有探討到,但是權勢性騷擾,這個其實是我們沒有辦法容忍的,尤其在這個特別權力關係裡面。
林:我覺得性騷就是很多東西相對在某一種模糊界線裡啦,然後證據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檻,但是不管怎麼樣在某種權勢的不對稱的一個權力關係底下,發生的不管是愛情,或者是性騷,其實它都不應該被容忍,我覺得這是應該已經有……
黃:都不能就這樣算了。
林:都不能就這樣算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篤定,可以大聲說出來沒有模糊地帶的東西。
黃:所以你當初在拍這齣戲的時候,有想過說會有人因為看了這齣戲就得到一些力量,就覺得我們不能就這樣算了。
林:我沒有想那麼多,說實話,應該是說我要小心是製作戲劇的過程其實很長,我們在閱讀文本,然後到跟每一個演員的溝通、到現場所有的討論,其實我覺得都不能夠用這一個念頭來驅使自己去做某些決定,就是如果我們一直帶著說,我們做的這件事情會改變社會,OK,那那種宣教的意味非常濃厚,然後我覺得……
黃:你覺得觀眾會看得出來,是不是?
林:我覺得一定會,觀眾真的很聰明,說實話,我誠心的喜愛我這個劇中的這些角色們,我希望他們看起來可愛,那個可愛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方式,所謂的可愛。
黃:可愛,怎麼樣讓你的角色可愛?
林:就是他其實我覺得跟真實生活一樣,其實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遇到一個新的人,如果我們夠瞭解他的方方面面,大概我們都很難真的完全討厭他,或者是真的就是覺得這個人百分之百的完美,當你想要讚美他的時候,你會有著對比,比如說他的個性很好,或者是他很善良,雖然怎樣怎樣,但是他很善良,對,所以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戲劇狀態就是說,你理解這些角色之後,你會有一種覺得「哎啊!阿龍啊,這個角色……你知道他就是……哎呀!太怎麼樣怎麼樣,可是他怎麼樣怎麼……」
黃:就好像是你的一個朋友,對不對?
林:對,你開始可以評論他,然後你會知道他的pros and cons(優點和缺點),然後這樣子的感覺,我覺得他其實就是一種可愛。
黃:是。
林:對。那其實回來討論說一個戲劇的拍的過程,我覺得太多小小的細節需要不停地做決定,尤其做為一個導演,那我覺得一種初心,就是我想要去喜歡這些角色,我想要去讓這些角色變得可愛,這個是我覺得我的初心,那我的初心不能夠變成是我想要透過這些角色把這個題目去影響社會大眾,我覺得這件事情會有很大的問題,它就會成為另外一個事情。
黃:對,其實我本來是很想要問你說,你是不是想要透過你的戲劇來改變世界?
林:絕對不會這麼想,應該是說不能這麼想,應該是說……
黃:你會有意識地讓自己不要這樣想嗎?
林:應該說,對。因為以這些題目來說……
黃:那表示你心裡其實是有這樣想啊?才要避免自己這樣想。
林:應該是說這些故事都有那樣子的……
黃:能量。
林:能量,所以我要很小心地去hold(把持)著那個能量去往哪裡去,比如說蒔媛姐的《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本,她相對來說,她自己都自己說自己是社交派編劇,她確實在她的本裡面,你會看到一些蛛絲馬跡是她非常想要大聲疾呼一些事情。
黃:是。
林:那我覺得我在跟她合作的過程當中,我自己站的位置就會是她給了很大的能量,批判的能量也好,倡議的能量也好。
黃:你要讓它內斂一點?
林:我要讓它放到背景去,或者是讓它變成是在服務角色的一個狀態裡,我覺得那樣子的狀態就是一個我跟她合作比較好的一個狀態,那跟小莉這次《人選之人》的工作狀態又有點不太一樣,因為我覺得小莉相對來說,這樣比較好像不太公平啦,但是我覺得可能因為他們有兩個編劇,所以他們自己彼此之間就已經有很多的討論了,所以在《人選之人》原始的劇本裡面,我想那樣子的想要倡議的這件事情,在他們自己的討論裡面,已經修到一個我覺得蠻舒服的一個狀態,那我要做的事情,其實再進去平衡一次,所謂平衡一次是因為他們有所謂的同志身份,那我覺得我自己也跟他們直接說,就是第一次我讀完全本,然後跟他們討論劇本的時候,我就說我覺得現在這個本很明顯很明顯是同志的一個視角,不管是站在翁文方那邊說的事情,或者是亞靜這邊的一些蛛絲馬跡,你很明顯的會感受到某一種端點的人想要說話的感受這樣子,那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但是我自己不是同志,所以我會進來一定會產生一個中和的作用,這我要先跟你們說,有些事情我會覺得我預判用這樣子的方式說出來,我覺得好像有點太大聲疾呼了,那我可能就會把它放到比較背景的聲音去,類似的討論,我們是有跟編劇做過這樣的討論的,可能相對就中和一些,比如說我自己很喜歡陳家競的角色,那是我在這個故事裡面非常容易去同理、同情的一個角色,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中年男子,那在處理這樣的一個角色過程當中,我大概就有意識地在做一種平衡感吧,對,因為如果陳家競這個角色小了,或者是相對邊邊了之後,你會發現整部片都在女性視角裡。
黃:嗯哼。
林:這個事情,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行,如果既然大家都認同這樣子的文本。對,但是回到一種我在詮釋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就會覺得說,如果一個中年男性的一種政治幕僚工作者的樣態,也可以在這個故事裡面,可以被相對比重足夠的份量去平衡這一切的話,它會變成一個相對更多人會覺得好看的東西。
黃:是,君陽因為《人選之人》大受歡迎,所以最近有非常多的演講,你覺得現場觀眾給你的反饋有哪些是超乎你原本預期的?
林:正確的來說,應該是還沒有到有很多就是我可以完全直接面對觀眾,因為電影比較多,因為電影《疫起》,我剛好也是在4月上映,所以那個過程當中,我們會去跑Q&A(問與答)宣傳,我們會去見到真實的觀眾,有些映後,那因為《疫起》是在講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在講跟疫情相關的故事,所以有很多比如他自己是醫護人員,或者他在過去3年的疫情當中,他遭受到某一些就像故事裡面的那樣子的人被隔離,然後被另眼看待,覺得因為疫情、因為病毒,所以把人不當人看這樣子的一個狀態,所以他們有很多很多的,比如我印象很深刻,有個機師是航空人員,他就是看完,然後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情緒化的在說,他在過去這兩年的時間裡,航空業所遭受到的一種不公平對待嗎?就是說就是你們……
黃:就大家知道他是機師,就會對他有一些……
林:我舉個例,他就是他直接講說,這好像不是他說的,但是因為同時間,比如說我聽報導者啊,他們同時有一個事情是機師在某個時間點被當成破口,那他們就被封在那裡,就是你不能回家,你要住在旅館,但是因為人力不足,他們還要被拉出去繼續執勤,所以封了14天不夠,然後可能到第12天,你又要再飛一次,飛回來又要繼續14天,這個事情他永遠見不到自己的家人。
黃:對。
林:他明明沒有問題,但是臺灣社會需要你在那裡,於是他好像就只能被封在那裡。
黃:好像被關起來坐牢一樣。
林:而最tricky的事情就是他出去執勤是運疫苗回來,這個事情就是會讓人不知道如何去面對這樣子,我被大家給鄙視,或者是被大家另眼相看,但是我做的這件事情其實是為了你們的。
黃:大眾而服務這樣。
林:哇!那個是……我聽到的時候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震撼感,就是雖然我都在講醫護人員的故事,但是我觸動了另外一些人,由他們自己生命經驗的一些反饋,這在電影有比較常……經常發生,以《人選之人》來說,因為它畢竟是在一個平臺上面,Netflix平臺上面去播出,所以我比較少一點這種面對面的觀眾的反饋,比較多是從網路上面看到很多人,譬如說他自己是政治工作者,然後他就會有很多很多的感觸,這個是可以分享,就是說有一些政治工作者,他們說他們就從頭哭到尾,或者是……
黃:終於有人看見他們的處境了。
林:就是我自己是很好奇他們怎麼能從頭哭到尾,因為我相信你跟著角色跟到後面,他的委屈你可以認同,但是有一位我不能說是誰,但是他就跟我說他看第一集就哭了,我說:「你哭點是什麼?」他說他哭的點是當第一天晚上張亞靜這個角色去到外籍配偶的家裡,然後等到最後是林月真這個主席,要參選的主席,然後來到他們家裡面,然後做了一個算是公關行為吧,去關心了今天被狗咬傷的這個事件,那她站在旁邊,主席點點頭跟她說謝謝,那一瞬間他哭了,我就想說到底動到你什麼呢?對,因為我相信一般人其實是不會對那個點有所觸動的,你如果在那個點就感動到落淚的話,我想那一定是跟你自己生命的脈絡有所相關,才會有這樣的觸動。
黃:甚至在他的政治經歷裡面,知道那是一件多麼辛苦的事情。
林:對,然後你也知道說,那樣子的事情也許多不容易,或者是你很期待某一個時間點自己……
黃:給你一點肯定這樣。
林:自己曾經被說謝謝,我沒有深問這件事情,但是確實好像有很多的不管是政治幕僚,以及我可以提一個是公務員。對。因為我有一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是公務員,他們在第一波的觀影的感想裡面,對我來說好像是一個蠻明確的一個標的,因為他們在做的事情也是跟大眾相關。
黃:是。
林:所以他們自己的很多狀況就是說,他們有很多的為難,比如說他們一樣就是每天工作過長,工時過長,然後他們做的事情又很小,而且常常又要以大局為重,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都很有既視感,於是那個討論他們就說,他們好像因為看了這個劇之後,相對來說好像更知道說,好像自己在做的事情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他們好像得到了一些鼓舞,我覺得這件事情我也覺得蠻印象深刻的。
黃:作為一個導演,你收到這樣的反饋,會覺得會有什麼感想?
林:會有什麼感想?我覺得意外比較多一點,我覺得意外比較多一點,就像我的初衷其實不是說要做社會倡議,我也不是要去獎勵這些職人們,但是它好像在某個程度上,只要大家相信這些角色,他的這些生活經驗就會變成跟你生活經驗有所共鳴,然後有些時候一跨圈出去之後,他就會形成一些反饋是你始料未及的。
黃:像《我們與惡的距離》,當時其實也引起非常多的討論,關於媒體的一些亂象,還有你每一集其實都有一些議題,透過主角包括這個思覺失調症,這樣的狀況也讓更多人瞭解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與惡的距離》當時也引起了非常大的旋風,那你自己怎麼看《我們與惡的距離》?
林:有點久了。
黃:因為有點久了,所以它的影響力還能夠持續在。
林:對。我覺得其實兩個層面吧,一個是文本的這一塊,就是那時候做了一個大家不會的事情,就是去用戲劇的方式,讓觀眾站到加害者的家屬那一面去,這個是一般人相對來說非常陌生的,而且會覺得你們罪有應得,就是我就算不厭惡你,我也不會同情你,那透過一個劇、一個一個故事,讓觀眾有機會去站到一個他平常沒有機會站到那個位子去,然後於是產生了心理上面一種同情或同理,可以這麼巨大的翻轉的一種感受,這個是我覺得在文本上面做到最重要的一個事情,那當然夾帶而來的關於新聞媒體的討論,這些東西可能都擴張了,不是只有這個,還有這個這個……,於是可以討論的事情就變得非常多,它就變得好像有機會在不同的族群,或者不同的議題的討論裡面都變成拿來舉例的一個對象,以致於到現在都還在討論它這樣,這是一個文本本身的層次,然後另外一個層次是回到臺灣戲劇的這一塊吧,我印象很深刻,那時候《與惡》一出來,然後很多人看了之後,發現整個不管是production value(產值),或者是說原來臺劇還可以做這樣子的題目,破開了某一種可能性之後,有一個業界的同事吧,就是直接feed back(反饋)說:「誒!你救了臺灣電視。」不能講我啦,應該說這部劇確實在那個時間點的出現,讓臺灣的戲劇節目有機會破開某些東西,我們不用再只守著愛情,我們也不用只守著小故事,我們有機會去碰到社會議題了,社會議題有人要看,只要你講得好,我們就可以擴張到另外一個層次去,它的可能性就變多了。
黃:是。而且它雖然是臺灣的社會議題,但是它因為碰觸到的是人性,一些普世的價值,所以它在國外的版權也賣得非常好。
林:對,對,對,到日本、韓國都賣了。對。然後韓國好像還有買了改編權,我不確定那個東西會不會往下走。
黃: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公共電視推出,我們也看到蠻多反饋是很多人捐款給公視,他們就說:「我終於覺得這個捐款很有意義,公視可以製作一個別的電視臺不敢做的戲。」
林:對,我印象更深刻是這個事情,就是說因為像這幾年這幾部戲都有跟公視合作嘛,那公共電視在臺灣戲劇的圈子,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因為商業電視臺有自己的立場,他們必須要把自己製作的東西給賣出去,希望有足夠的回收,那這樣子的思維完全沒有問題,但是也就因為這樣,所以常常有一些題目就會變得想碰又不敢碰,那對於公視來講,因為站的位置完全不一樣,所以也不是說不管回收,對,我跳題就是《人選之人》最重要的一個事情,對我來說是我們可以跟投資者交代說我們有賺錢,因為Netflix買到全球版權,然後他們認可這樣的production value跟這樣子的故事是有機會跨文化的。
黃:是。
林:那所以讓後端這些投資者們有相對應的回收,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與惡》沒有,很清楚知道《與惡》那時候是一個在社會上引起很多的討論,然後它的錢某種程度上從前瞻預算來,那這些東西都來自於一個我們其實不期待這個東西有所回收,那當然它後來回收的不管是聲音上面、討論度上面都不錯,但是我不清楚它的經濟上面的回收是不是能夠打平?但是回到一個臺灣產業的健康度來講,我覺得一個故事它是需要有這樣子的活水,它必須run(跑)起來,我花了5000萬拍,它就應該要能夠收獲……
黃:至少5000萬可以回來,甚至賺到一些。
林:對,這很重要。對,那至少在《人選之人》這部戲裡面,我們有達到這個事情。
黃:因為它也會讓之後有更多的投資者願意投資臺灣的影視產業。
林:對,這極度重要,那另外一個程度也是說既然有人願意買,就表示有人願意看,那表示這件事情是可以就是繼續做下去的。
黃:是。而且它在Netflix上的排名都非常好,公共電視下半年也會推出,會有更多的觀眾可以觀賞。但君陽的對於這個職人劇,你拍過了這麼多職人劇,你的感覺是什麼?職人劇它的對臺灣的戲劇產業,它的意義在哪裡?
林:我其實很難說這些劇真的是職人劇,說實話,就是說我有點到啦,譬如說《我們與惡的距離》。
黃:新聞業。
林:新聞業,然後心理師、社工,它都稍微點到了,然後但是我們跟從前的日劇不太一樣,職人劇從前以日劇為大宗嘛,他們很習慣去鑽進某個產業,把那個產業的辛酸苦果把它給拍攝出來,職人劇其實是某個程度上我們是從日劇學來的嘛,那我們這幾齣戲,其實都沒有一個單一的職業。
黃:不只是單一的職業。
林:對。它都是說這個故事需要去討論到的人有這麼多,那以《人選之人》政治幕僚來說好了,其實政治幕僚有很多不一樣的人,那這個故事裡面我們也同時要去碰到,比如說競選者,那些其實你又不能講說他是政治幕僚,我覺得啦,就是職人劇,先不講它到底是不是,但是我覺得在做這幾齣劇的過程,可能因為《與惡》那時候開啟了一個事情就是,蒔媛姐做的田調非常紮實。
黃:對。
林:而這個紮實回應在《我們與惡的距離》那樣子的一個劇種裡面,相對寫實的東西,因為它寫實,因為它紮實,因為它跟真實世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它丟出去的討論就會變得非常紮實,跟它可以影響的層面就比較遠,至少大家不會說,雖然它戲劇很誇張啦什麼的,那個不是真的,那我們來討論那個可以討論的東西,它那時候的做到的事情大概就比較是說,這是真的,或者是我不管它是真……這是很值得討論的,我們現實當中就是會遇到這些困難,於是它就產生很大的討論,那我們講的是田調的一個態度跟重視的程度。
黃:紮實度。
林:後來在《茶金》,比如說我們在碰到茶農跟可能我們要去做歷史的調研,也是一個方向上的紮實,然後跟譬如說在《人選之人》,我們要去做到跟另外一群人的一些田調的另外一種紮實,所謂田調的紮實是我覺得在所謂的職人劇裡面,我會……
黃:成功的關鍵。
林:最appreciate(欣賞),我可能不講成功啦,我覺得純粹就是講說我自己覺得我很感謝的事情,因為這些過程當中都因為拍了這些戲,所以我更認識這世界上的另外一群人,也許是從角色認識,也許是從田調的過程當中認識,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對,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的生命經驗沒有那麼豐足。對。所以在短短的這3、5年的時間裡面,我有機會碰到茶農、茶商,我有機會去碰到心理師、社工師,我有機會去碰到政治幕僚工作者,然後跟立委吃飯,跟議員吃飯這樣,前兩個禮拜我還跟議員唱歌這樣,對我來說這個是一個生命上面很大的一個豐厚,OK,我雖然不能說我完全理解了他們,但至少我見過面、吃過飯、聊過天,對於接下來的不同的可能創作,我覺得它都開啟了一些新的一些養分。
黃:就可以吸取更多不同的人的生命經驗。
林:嗯。
黃:所以你自己對於戲劇是從小你就最喜愛的領域嗎?
林:其實還好耶,小時候都是看漫畫啊,我喜歡看故事這是真的啦,就是從最小的時候,漫畫,然後金庸、古龍,看著武俠小說長大的,大概是……我不確定別人是不是這樣,但至少我的成長經驗是這樣,就是整個國中時期大概都膩在金庸跟古龍,然後從金庸、古龍一直看到梁羽生、四大,然後把它全部都看完了這樣子。
黃:那後來怎麼不是當編劇?或者怎麼沒有當演員?你的外型也非常適合當演員。
林:我沒有辦法當演員啦,我很清楚知道,就是我有客串過,然後因為我很清楚知道說演員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某個程度上的忘我,但是你要能控制那個忘我,你要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去講這些角色,我記得那時候客串的時候,我很清楚知道我是我,我只是在講這個角色。
黃:你跟這個角色是有分離的。
林:那是一個專業,要想辦法用各種方式去帶入,然後去演出,這個都很困難。對,那編劇我自己其實下筆很慢,我講話好像很快,然後好像會不時的有很多事情一直衝出來、一直衝出來,但是回到我自己要字斟句酌地寫東西的時候,它就會變成一個很緩慢、很緩慢的過程。
黃:會考慮很多。
林:會考慮很多,考慮太多。對。我清楚知道,那是我考慮太多的一個過程,但是我掙扎不出來,所以我比較傾向跟不同的編劇合作,那也是好處,就是說不同編劇有不同的在意的事情,那我好像是一個適合做增幅器的一個導演,就是你對這件事情感興趣,如果我也能夠在這樣子的故事裡面找到我自己的觀點跟我感受得到的一種感動的話,那我們就把這感動說出來,我可以幫你把這個事情給放大,把它變完整。
黃:是。
林:我想這樣子的合作,我還蠻愉快的在這幾年的過程裡。
黃:是,君陽一路從《愛的麵包魂》、《愛情算不算》、《愛情白皮書》、《我們與惡的距離》到《茶金》,到《人選之人》到電影《疫起》,其實你拍的戲都非常的叫好叫座,你覺得這樣走來,你已經摸索出一些心法了嗎?
林:我只能說有一些導演手法,大概有一種越來越熟悉的狀態跟比較自在的狀態,但是因為每一次、每一次的挑戰都不一樣,就像《人選之人》,當時在立案我們要做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包含政治、職人劇,然後裡面會提到的性騷擾,這些東西其實都有一種「哇!沒有人做過」,或者至少就算有人做過,也沒有人這樣子的組合,然後我們也期待自己做的東西是跟別人不一樣的,於是那個每一次新的案子都會想要讓它有所不同的狀態,我也不確定我現在掌握的到的這些所謂的導演的風格或技巧,它會演變,還是說它會因為熟悉的這個筆調之後,它會重複不停的再被利用,這個我覺得是我現在當下的一個題目。
黃:就還在摸索。對,那為什麼你留在臺灣拍戲?你覺得臺灣吸引你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林:我覺得這幾年這幾部戲應該就還蠻明確的就是可以感受到一個事情,就是我在乎這些故事從在哪裡發生?
黃:是。
林:然後在哪裡被聽到?對。所以也不是說我一定要選擇在臺灣,就這個是我家嘛,所以我在臺灣講這些故事,我覺得是一個所有的事情都理所當然,所有的事情都水到渠成的狀態,有時候會討論,譬如說在臺灣社會會有這樣子的人嗎?我舉一個例子,《人選之人》第一集陳家競他狂奔出去,誒,還是第二集?狂奔出去要去回家去見老婆。對,要回娘家的老婆,在大廳被火龍果汁撞到,被一個路人撞到,那個是我加的,編劇寫了一個他狂奔,然後要去找到那個妻子的這個過程,或者說我想要讓那個陳家競再衰一點,然後他們就說:「那不然撞到一個人?」我覺得好啊好啊,那撞到什麼?然後他們就說火龍果汁,我就說好啊好啊,這是一個談論這樣討論的過程,所以我們用一場戲讓陳家競更狼狽。
黃:是。
林:那個時候是一個戲劇上面的要求,我想要讓這個人更狼狽,於是那個狼狽就會一路貫穿到晚上,為什麼他會這麼的沮喪、喪志在那邊唱歌這樣子,中年男人那樣子,那說不出來的狼狽,目的是這個,但是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們在拍那場戲的時候,我想要達成另外一個效果,就是臺灣人被撞到的時候會怎麼樣?如果是韓國人,那時候撞到,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大概就開始罵髒話了,可能就會是這樣子一個表演狀態,那是符合民族性,那臺灣人會怎麼樣?那時候我在現場試撞的時候,我就覺得一定會是不停地道歉,就是那種先不管誰錯,但是先說對不起。
黃:先道歉。
林:先說對不起,到底誰錯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先說對不起。
黃:這是臺灣人很可愛的地方。
林:可愛啦,好處是可愛,然後壞處可能有點鄉愿啦,但這就是我覺得……看到會覺得會會心一笑的東西,那在現場我自己笑得很開心,他們也演得很自然,我就說你回答你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要在臺灣拍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我最瞭解的就是臺灣人的某一種秉性,那這些故事、這些人物想要他們紮實,或者是像是個真實的人物,我可能比較容易對標的就是臺灣人的樣子、樣態。
黃:是。
林:那拍臺灣的故事給臺灣人看,這是我現在在這一個脈絡裡面做的感覺相對紮實的事情。對。
黃:但你現在不只是面向臺灣的觀眾?現在是面向全球的觀眾?
林:對,這就是一個需要轉化的事情,就是我不講沉溺,但是確實這個東西講到一個位置之後,我能不能夠讓它變成輸出?或者是能不能夠讓更多的人有類似的感受?
黃:可以讓全球的人都被觸動。
林:也許,這是可能下一個階段的目標吧。
黃:在臺灣拍戲啊,這是你的家鄉,你想要把臺灣的故事講得很好給臺灣人看,你覺得在臺灣拍戲面臨的這個挑戰跟困難是什麼?
林:我覺得現在目前全世界都一樣,就是一樣就是因為OTT(串流媒體服務)平臺的崛起,然後這幾年其實讓大家找到了熱錢以及放映的管道,觀眾開始大量地湧入OTT平臺,不管是哪個平臺、很多個平臺,那這個關於模式的改變就造成了大洗牌,那也造成了很多新的商機,然後新的可能性出現,比如說以前不管在哪個國家,我們在電視臺裡面拍戲一定會有所謂的審查,不管是商業上的審查,或者是說在某些國家機器裡面會有做出的審查,這個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也會有一些些相對應的這個要到什麼程度這樣子一個討論,那OTT沒有,對,OTT的平臺就會回到只要有人願意買,我們就願意賣。
黃:沒有什麼暴力色情的界線嗎?
林:暴力色情的界線會回到平臺自己的機制,比如說我可以家長模式,讓我們搜尋不到,但是如果我就是衝著這個東西來的,我買的到我要買的東西,它有另外一些商業機制的可能性這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平臺裡面,就會有相對比如說真的把性講得鮮血淋漓的東西,那是另外一個需求嘛,你不能說那個性就不對。我一直覺得日本在我成長過程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他們把性放在很前面,他們不避諱去討論人的慾望裡面有性這件事情,而他們把性當作一個可以買賣的商品,明買明賣不犯罪這件事情,那既然它成為一個有制度的狀況,它就可以被疏導去一個相對舒服的地方,那有時候我覺得我們有時候會太……就不能講不能講,不是每天都在想要談戀愛,然後成長過程當中,你就是這些慾望。
黃:人就會有這樣的慾望。
林:對啊,有什麼不好講的?那其實回到現代OTT平臺,它解放了很多的這些規則,那它就產生新的市場的需求、供需,那臺灣的狀況就是我覺得跟其實很多人一樣,就是說好像大平臺起來做,我們都會依附大平臺而生,而偏偏大平臺這幾年也會遭遇它自己的困難,他們自己的預算也不足,或者是他們可以買下來的,所謂的大製作的東西也有一個天花板在,那於是你不能夠無限上綱的一直依賴大平臺,這是一個供需的問題啦,它比較回到商業機制,所以現在目前全世界都一樣啦,像上禮拜不是看到一個韓國他們好像現在有八十部還是一百部劇已經拍好了,但是平臺不願意買單。
黃:對。
林:那臺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就是有一些東西拍完了之後,其實平臺會覺得說,欸,我們這邊量能已經這樣,你很好,但是我們買不起了,我們今年的quota(配額)到這裡,不然明年請早這樣,但是明年又有明年的規劃跟計畫,可能有很多東西是排在明年要上的,可能更大,這是一個市場上的問題,那臺灣在面臨的事情就跟全世界的事情其實差不多,那產業面上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覺得我們有自己的know-how(知識),這些know-how不完全能夠跟世界接軌,就是譬如說編劇的時候的一些邏輯、結構,跟一些運作的模式,比如說我們可能現在會去取經所謂的好萊塢,或者是美劇,他們有所謂的編劇工作室,這樣子的一個工作的流程這樣子,很快地去把一個故事在很標準的市場裡面去運作出來的東西,在臺灣我比較沒有經驗到任何成功的例子,有人想要去嘗試,但是基本上我覺得跟語言、語種跟訓練都有關係,臺灣至少我們現在都用中文,它有很多歧異跟模糊的東西,這個是這個語言本身就有的東西,所以它很難寫得像英文那麼精確。
黃:所以它很難像一個生產線一樣,每個人負責一部分,然後就把一個劇本產生出來。
林:對,我不確定就是……可能還是有相對應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其實跟我們現在是用中文在創作,其實是有相對的關係,那我們會經驗到比如說我們用中文寫,然後翻譯成英文,請國外的編劇看,然後他們給的feed back兩邊對不起來。對,因為英文思考跟中文思考真的不太一樣,這是一個對我來說,我很現實卡到的問題,我們希望我們的東西能夠跟……
黃:能夠輸出國際。
林:那找了國際的顧問來看的時候,他們給的feed back其實你吃不下來,因為你吃下來你會覺得這個就不像臺灣的人說的話,或者是臺灣人會做的事情,或者是這個角色好像就是他們哪裡怪怪的,他開始混得……
黃:會有一些文化差異。
林:這些文化差異需要去處理,這個是臺灣面對世界的時候的一個關卡,然後再來就是回到很製作面的事情,我們的資源,比如說臺灣沒有足夠大的片場,對,然後我想要拍時代劇,通常都只有兩面牆,或者得要一直去找古蹟,這件事情終究不可解,如果我們的故事需要被解套,各種想像力的話,我們需要片場,我們需要新的拍攝技術,我們需要更多跟國外合作的各種可能性,把它打開。
黃:所以下一部戲想要拍什麼?
林:下一部戲想要拍什麼?這也不是我能決定的。
黃:已經開始籌備了嗎?
林:現在在做那個啦,《與惡2》的前置。
黃:太好了,已經期待好幾年了。
林:對,蒔媛姐這是嘔心瀝血地做了另外一番非常深入的田調,那我們也期待能夠如期的進行。
黃: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推出?
林:不敢講,這就真的不敢講。對。對。因為也是跟大慕合作,那大慕這邊製作人昱伶姐,合作關係裡面有一塊,我們現在都已經放棄的事情,就是我們就是快不了。
黃:對,為什麼快不了?我記得這個是2019年《我們與惡的距離》大獲好評之後,大家就一直敲碗等第二季,就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們不能趁勝追擊?從2019年到現在四年了。
林:我覺得啦,一個事情是它畢竟不是所謂的類型劇,然後當初蒔媛姐在寫第一季的時候,也沒有想過這些人物要留尾巴,所以1的結尾就結尾了,那些角色戲劇裡的人生歷程已經走完了,我不會用這些人重新去開一個他們之後怎麼了,或他們之前怎麼了。
黃:不是前傳、後傳的概念。
林:對。對。對。對。《與惡2》原則上它作為是一個全新的故事,在同一個宇宙觀、世界觀裡面,然後在同一個大題目底下,我們一樣在討論這個社會上面,在討論善與惡的那個模糊界線,然後跟每一個人其實在這裡面都是一份子的這些基本的態度,我覺得跟《與惡1》是一脈相承,但是想要講的事情完全不一樣,那這個就很需要時間,它等於是另外寫一個,它不是那種延續一個角色,我可以很快就開展,想像他接下來往哪裡走,它確實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黃:好,那我們只能期待《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二季。
林:希望大家的這個願力能夠讓我們一切順利。
黃:可以讓你們更快一點。
林:快不敢講,快真的不敢講,但是就是慢慢地順利也是一個好事。
黃:是。精彩最重要。
林:對。
黃:謝謝君陽今天的分享。
林:謝謝。(校對:李建甫|更新:2023/07/20)